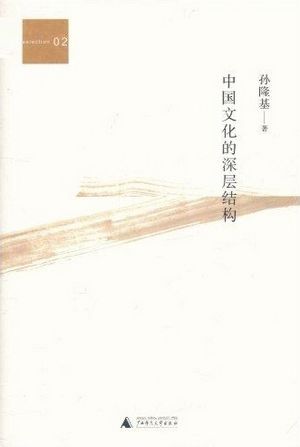序言
十年前,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,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——这一句话,把我推到今天。 话很普通,只是一句常识,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,“人”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,被概念化,被无知和偏见遮蔽,被模式化,这些思维,就埋在无意识之下。无意识是如此之深,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,对自己也熟视无睹。 要想“……
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
二〇〇〇年,我接到一个电话。“我是陈虻。”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,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。 “谁?” “我,陈虻……没给你讲过课?” “你哪个单位的?” “嘎……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,找你合作个节目。”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。 我打量他……
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
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,到“新闻调查”的第一天,晚上大概九点,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:“我来报到。” 张洁说:“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。” 我说:“我想做。”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。之前几个月,“非典型肺炎”已被频繁讨论。最初,媒体都劝大家别慌,但到了四月,我家楼下卖……
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
进“新闻调查”的第一天,有个小姑娘冲我乐。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,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,挂着两条耳机线,走哪儿唱哪儿,一条短裙两条长腿,叽叽呱呱,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。 她二十三岁,痛恨自己的青春,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,总用白唇膏盖着,“这样比较有气质”。哦,这好办,我叫她老……
第四章 是对峙,不是对抗
二〇〇三年九月,张洁搞改革,“调查性报道”成为“新闻调查”的主体,以开掘内幕为特征,采访会很刚性,开会的时候他发愁:“柴静跟我一样,太善良了,做不了对抗性采访。” 老范接下茬:“都不见得吧?” “真的,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。”一屋子人,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。 “她?”天贺……
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
六月的广东,下着神经质的雨,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,野茫茫一片白。草树吸饱了水,长疯了,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,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,全是蛮暴之气。 我们在找阿文。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,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。戒毒所把她卖了,卖去卖淫。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,记者向警察举报……
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
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。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,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,全是她丈夫留下的。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。大瓦房,窗户窄,焊着铁条,光进不来,要适应一会儿,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。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,团成一团僵在床上。十几年间,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……
第七章 山西,山西
海子有句诗,深得我心:“天空一无所有,为何给我安慰。”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。小孩儿上学,最怕迟到,窗纸稍有点青,就哭着起了床。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,穿过枣树、石榴和大槐树,绕过大狗,我穿着奶黄色棉猴,像胖胖一粒花生米,站在乌黑的门洞里,等学校开门。 怕黑,死盯着一天碎星星,……
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
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。 他想解开网。母亲冲他喊:“不要放,放了又吃果子,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。”一群村里的孩子,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,手里拿着剪刀。不知怎么“呼啦”一下进了院子,都盯着那只麻雀。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,说“这个好吃”,伸手就去够。 老陈一着急,把网……
第九章 许多事情,是有人相信,才会存在
二〇〇六年二月底,我接到通知,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。 被惊着了,因为在“新闻联播”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,叫“柴静两会观察”。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,倔下巴,一丛黑发又硬又直,大眼睛毒得很,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,“柴静比想象中瘦小,像个初二女生。有……
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
二〇〇四年,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。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,人多嘴杂听不太清,我索性站起身问:“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?” “不同意!”居首一位农民说。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:“不同意!不同意!” 我说:“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。”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,老人家的手攥……
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
二〇〇六年两会期间,网上有段视频热传,是一只猫被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踩死的过程。 视频里,她脸上带着笑,照着它的眼睛踩下去。那只猫的爪子微微举起,无力地抓挠,直到被踩死。她踩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摄像机,录下的视频被拿来在网上收费观看。 当时在忙两会,不及细看,路上听到出租车里电台主持人播报这件事,说:“……
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
一天傍晚时分,史努比打来电话:“吃饭?” “行。”我说,“我请你,正打算下楼吃呢。” 他顺竿上:“不成,你做。” 我气笑:“凭什么呀,只有方便面。” “不行。” “那就下挂面。” “挂面成。”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,连理都不讲。 只好去超市,买只鱼头、料酒、……
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
二〇〇七年,陕西农民周正龙称自己在一处山崖旁,拍到了野生华南虎,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这些老虎照片,宣布已灭绝二十年的华南虎再现。 外界质疑很多,一些人觉得照片上褐红色老虎太假,一动不动,两眼圆瞪,呆呆地顶着大叶子,不像真的,但也只是狐疑,没有定论。 我们开会,讨论做……
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,汶川地震。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,没有网络,没有电视信号,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,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。 打电话请示领导。张洁说:“别回来了,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,现在做不了专题,都是新闻。” 我发短信给老郝:“怎么着?” 她说:……
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
二十出头,在湖南卫视时,我采访黄永玉,问他的“人生哲学”是什么? 他说两个字:“寻常。” 我心想,这也叫哲学吗? “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,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?”他说,“因为她什么都有,只缺寻常。” 我听不懂。 北京奥运,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(MPC)的记者证……
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
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:“你从湖南卫视来,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?”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。 陈虻指指桌上:“这是什么?” “……烟?” “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,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。他说行,你等着吧,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,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,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……
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
卢安克坐在草地上,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,打来打去。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:“不要这样。” “为什么不要这样?” 我就差点说“阿姨不喜欢这样”了,绷住这句话,我试图劝他们:“他会疼,会难受。” “他才不会。”他们“嘎嘎”地笑,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。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,不作声,……
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
二〇一〇年年尾,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。陕西西安,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,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,导致张妙主动脉、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,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。 舆论分歧巨大,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……
第十九章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
从进台开始,发生争执时,陈虻总说:“你的问题就是总认为你是对的。” 我不吭气,心说,你才是呢。 他说:“你还总要在人际关系上占上风。” 咱俩谁啊?从小我就是弱势群体,受了气都憋着,天天被你欺负,哪儿有你说的这毛病? 我采访宋那年,他十六岁,在抑郁症治疗中心的晚会上参……
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,我接到同事短信:“陈虻病危。” 去医院的车上,经过新兴桥,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乱晃,我迷糊了,两三个月前刚见过,简直荒唐……不会,不行,我不接受。我不允许,就不会发生。 一进门,一走道的人,领导们都在,我心里一黑。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,他们……
后记
三年前,我犹豫是否写这本书时,最大顾虑是一个记者在书里写这么多“我”是否不妥,六哥说不在于你写的是不是“我”,在于你写的是不是“人”。 这本书才得以开始。 当中数年我停停写写,种种不满和放弃他都了解,不宽慰,也不督促,只是了解这必然发生,我才有气力写下来。书稿完成后他承担了大量编辑工作,编辑时他曾说……